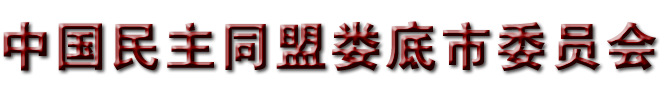為了承擔而前行
為了承擔而前行
——游宇明訪談錄
(記者:《雜文選刊》下旬刊編輯部主任李慶玲,以下簡稱記者)
記者:您創作過詩歌、散文、隨筆、小說、雜文等,這些文學體裁對您來說有著怎樣不同的感情和意義?
我寫作的多體裁,首先是源于一個時代的文學激情。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進大學中文系時,文學正被人頂禮膜拜,無論寫什么作品都是一件讓人羨慕的事,很長一段時間,我只關注是否寫出和發表了文章,而不在乎它是詩歌還是散文。我是從詩歌開始自己的寫作生涯的,但選擇寫詩,只是因為青春的激情最適合用這種體裁去表達,而不是因為自己對詩歌特別愛好。在省級以上報刊發表了100多首詩歌之后,某一天,我突然覺得散文、隨筆更適合表現我在日常生活中產生的細膩情感,更便于構筑自己的心靈高地,于是開始了第一次創作轉向,那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寫小說則是更晚的事,純粹抱著寫著玩的態度,沒有刻意追求。在我操持的幾種文學體裁中,小說是成績最小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我感覺自己對政治、文化、教育、社會等領域的事情有許多想法,這些想法不太適合用散文、隨筆表達,在我的理解里,散文、隨筆主要是一種讓心靈溫暖的文字。我后來花了不少時間和精力在雜文創作上,主要是為了滿足內心日益增長的批判意識,體現某種公民情懷。換句話說,作為一個寫作者,我不一定需要介入雜文;但作為一個有良知、有血性、希望有所擔當的知識分子,我必須毫不猶豫地走向雜文。
記者:是什么機緣使您對雜文情有獨鐘呢?
寫雜文之前,我已在省級、中央級報刊發表了好幾百篇(首)散文、隨筆、詩歌,本來可以沿著這條路走下去,但兩件偶然的事情促使我在雜文上用心:一是初次寫的雜文被1999年8月14日《中國紀檢監察報》“清風文苑”刊用;一是雜文《盯盯另外的人》被2000年10月《雜文選刊》轉載。1999年8月以前,我從未寫過雜文。有次從電視新聞上看到西部某縣以縣財政困難為由,一年多時間砍完一片原始森林,而肩負保護森林使命的林業檢查站居然只要盜伐者交錢就可放行,內心充滿憤怒,當夜寫成一篇雜文,第二天就將它寄給《中國紀檢監察報》,沒想到不到一個星期文章就出來了。我的第一篇雜文發表得如此順利,其實是與我以前大量寫過詩歌、散文、隨筆分不開的,已有的寫作實踐鍛煉了我的角度意識與語言技巧。《雜文選刊》轉載《盯盯另外的人》,更加強了我寫好雜文的信心。現在我的雜文也算有點收成,相當數量作品被《雜文選刊》、《雜文月刊》、《讀者》、《書摘》、《青年文摘》等著名報刊轉載,不少作品進入《中國當代雜文二百家》、《讀者人文讀本》、《中國年度雜文》、《中國雜文精選》、《中國散文排行榜》等權威文學選本和大學教材、中學語文閱讀教材,但在2000年那個時候,我的雜文“養在深閨人未識”,能被《雜文選刊》這樣的權威文摘刊物轉載,其驚喜,跟一個人只報了普通大學卻被重點大學錄取頗相類似。
記者:您現在的寫作偏重于散文與雜文,在很多人看來,二者在寫法與特質上似乎有著天壤之別,您有哪些筆耕心得呢?
我在寫作上確實長期散文、雜文并重。散文與雜文在寫法與特質上的區別非常明顯。我覺得優秀的散文首先必須充滿溫情,字字句句都能讓人體會到生活的瑰麗、人性的美好;其次,文筆一定要特別優美,讓讀者一進去就能被作品中的氛圍所感染。再次,它應該有巨大的藝術張力,散文的線索可以單純,但蘊含的思想應該盡可能豐富,使不同生活經歷的人讀出不同的味道。雜文呢,它絕對要直指現實直擊人心,應該痛快淋漓地告訴讀者社會的病灶在哪里,我們如何根除它。雜文可以因為藝術原因使用“曲筆”,但不可以缺少本質的血性和剛烈,不可以缺失思想上的振聾發饋。當然,散文與雜文在精神的深處是相通的,它們都要弘揚關愛、善良、悲憫、尊重、人性等人類的普適價值,都要引導人們正確地處理人與自身、人與他人、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都要教會人們如何去熱愛值得熱愛的事物。一個人從散文思維過渡到雜文思維,其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樣困難。
記者:您的作品多題材重大,將眼光鎖定政治體制、權力腐敗等,如《背景意識與權力走私》、《蔣介石的“私法”》、《當無知附上“絕對權力”》、《漫談某些“不到位”的改革》等,您怎樣看待雜文的選材?
一個社會的核心問題就是官員權力與民眾權利的博奕,按照現代政治理念,以官員作為依托的政府不是我們的衣食父母和救世主,相反,我們倒是政府的衣食父母、是決定政府命運的關鍵力量。政府當好了守夜人,不值得我們特別表揚,那不過表明它盡了自己的本分;政府沒有做好該做的事,甚至監守自盜,借助權力大肆揮霍社會資源,民眾就應該批評它,民眾的批評有許多種,通過雜文的形式進行輿論監督就是其中之一。在我們這個社會,官員的權力遠遠比民眾的權利強勢,這就是我寫雜文時喜歡選擇政治體制、權力腐敗等重大題材的原因之一。大家都意識到社會的核心問題是什么,他們才會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關注官員如何使用權力,社會的監督力量才會充分培育起來。雜文當然也可以選擇小題材,一花一草之小、一燈一線之微,都可入筆,但我覺得在一個威權社會,對權力的警覺應該高于一切。野蠻拆遷、讀不起書、看不起病、買不上房、司法不公、貧富懸殊等等社會病態,哪一樣沒有權力胡亂伸手的影子?雜文自然不能因為題材的大小而區分意義和價值,但我們必須承認生活中有些問題更關系到國家、民族的基本走向,更值得雜文家投注自己的精力和熱情。
記者:題材的選取至關重要,而如何使雜文“文質彬彬”,則更需功夫與火候,您的作品多以恰當的事例增添其形象性、可讀性,同時注重形式上的多樣化,能否談一下您的創作心得?
“說什么”確定之后,“怎樣說”就變得特別重要了。其實,任何文學作品都必須注意一個“怎樣說”的問題。官員的工作報告只要用詞準確就行,他們可以用行政權力去推廣自己的思想;但雜文家的作品用詞準確遠遠不夠,原因很簡單,雜文家手中無權,人家讀你的作品必須依靠內心的喜歡。要讓讀者喜歡你的作品,你就必須考慮如何讓作品變得“好讀”,即要注意寫作的藝術。我的雜文引入事例也好,注意形式的多樣化也罷,其實都是想讓雜文寫得盡可能“好讀”一些,使讀者樂于接受。
記者:借古說今是您雜文的一大特色,引入歷史上及近現代的人物與史實,對現實進行針砭批判,這種風格是如何形成的呢?
歷史就是過去了的現在,與現實一脈相承,我2010年在湖南的《老年人》雜志開了一個專欄,欄名就叫“以史為鏡”,“為鏡”,其實就是歷史對我們的最大意義。我寫雜文喜歡引入歷史上或近現代的人物、史實,對現實進行針砭批判,從“道”的角度而言,是因為我發現雖然時間過去很多年,但歷史上出現過的一些不合理的東西,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依然大量存在,比如領導者專權、民眾言說渠道不暢、舉報者被報復、官員以權謀私等等。我希望通過自己的這類文字讓讀者產生一些痛感,喚醒他們改變歷史痼疾的愿望與決心。從“術”的角度看,寫歷史題材的雜文,因為當事人已遠去,思路打得開,發表也較少受到干擾;再說,歷史事件本已經過沉淀,歷史題材的創作自然也更經得起時間的淘洗。而讓自己的作品經住歲月的考驗,幾乎是所有寫作者的一種心結。
記者:雜文貴在敏銳的發現,在《皇權下的“規矩”》中,您有這樣的觀點:“有規矩,一些人從中得利,他們會看成是制度的產物,沒有規矩,什么事都由皇帝一個人說了算,有人得了好處,他們就會把它看做是皇帝的恩典,死心塌地地為皇帝服務。”這一悖論,仍存在于現代社會中,這也正是權力的迷人之處。您能否結合您的創作及當今現實談談您的看法?
權力的暗箱操作,是中國幾千年的政治一直沒有解決好的一個問題。我在《不守規矩的權力就象小偷》、《陳濟棠的迷信及其他》、《獨裁者的救生圈》、《公權與私恩》、《好官圖騰》、《值得商量的“力排眾議”》、《中國不存在利益集團嗎》以及您上文提到的《背景意識與權力走私》等雜文中,就表現了對權力私下運行的深深憂慮。我覺得未來中國的政治改革,不管具體的制度如何設計,關鍵要在以下三點著力:一是及時制訂以民意為旨歸、公平合理的社會規則;二是督促權力徹底公開透明;三是使暗箱操作的人付出足夠的政治、經濟代價。皇權下的“規矩”之所以成不了真正的“規矩”,就是因為皇權至高無上、不受任何制約,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中國現在經濟上已經慢慢走向開放,如果在政治上再延續計劃經濟時代的一些做法顯然不合時宜。市場經濟最大的意義,就是它培養了我們經濟資源由市場配置的觀念和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意識。歷史早已證明,當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呼喚政治的自由民主,要求充分保障公民權利,會成為民眾的一種自覺行為。而暗箱操作必然助長權力的胡作非為,直接引發惡性群體事件。一句話,現在搞以制衡公權、張揚民權為目標的政治體制改革正是時候。
(原載2010年10月下《雜文選刊》“訪談”)
- 上一篇:曾芝紅獲“婁底市好媳婦”榮譽稱號 2011/3/9
- 下一篇:情系農民,幽默清新 2010/10/20